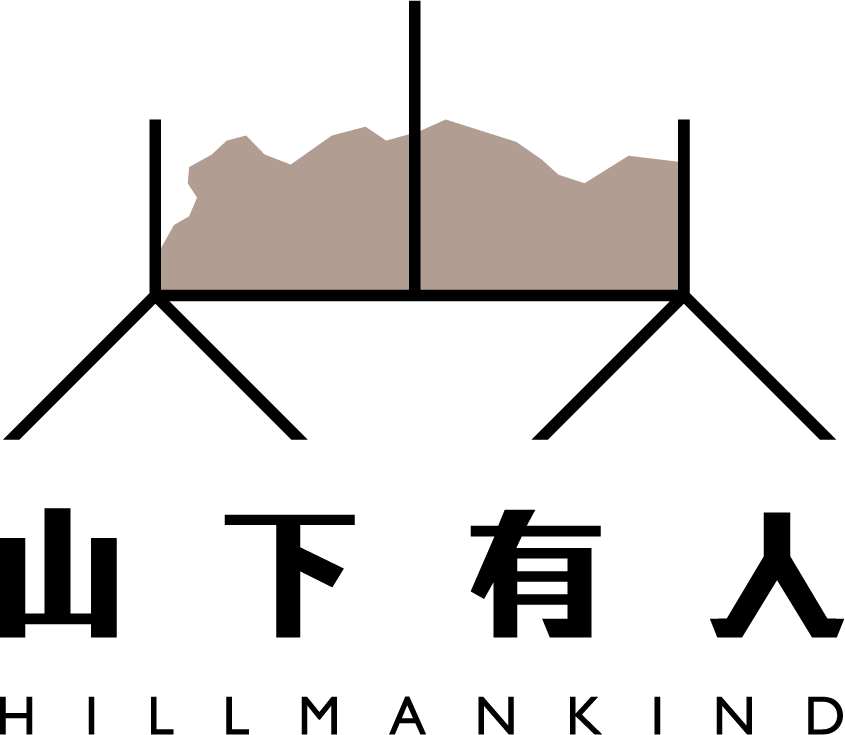聾人的子女,即使健聽,但成長路沉寂難行,譬如牙牙學語的時候,就要跟父母分開,搬去健聽的親友家中寄居;譬如六七歲就要替父母「說話」,交電費去銀行處理種種世務。「香港聾人子女協會」說香港無聾人政策,亦無統計聾人子女的數目,粗略估算數以萬計,極需支援,尤其在學習發展和家庭輔導上。
常人的生活有聲有色,難以想像無聲的世界,反之亦然。曾經在協會擔當義工的 Yolanda ,她幫聾人子女補習,最印象深刻是疫情期間,小朋友去了茶餐廳上課。
Yolanda 說明明約好了時間,上 Zoom 補習,但有一位媽媽帶兒子到茶餐廳食飯,然後即場用手機開 Zoom 跟她上堂。那一刻,茶餐廳熙來攘往,人聲嘈雜,怎樣上堂?啊…媽媽根本聽不到。Yolanda 說媽媽只是大力扭小朋友的頭,要他一直面向熒幕,要他盯著老師的嘴型,像聾人閱讀唇語一樣,但小朋友掙扎,聽到媽媽發出生氣的聲音:「媽媽好似唔記得咗小朋友係聽到野,不停夾住佢對耳仔、擰佢個頭望住我,咁佢梗係唔會好溫柔……我好心痛,覺得媽媽體諒唔到呢個小朋友,佢點會學得好。」當下,Yolanda 只能說無問題無問題,建議回家再上堂,又勸媽媽不要責怪兒子不專心。
她說小朋友是健聽,讀小四,跟一般學生無異,但來自單親家庭,聽障媽媽有情緒困擾。Yolanda 記得初次見面,媽媽以含糊的發音責備兒子做功課不聽教,再靠電話不停打字表達,情緒激動,又傷心又勞氣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,加上聽障就難上加難:「佢哋溝通又難,加上好多都係基層家庭,都係打同鬧。小朋友讀書差又無人教,成件事不斷 loop 落去。」

Yolanda 的義工工作就是補習,協助聾人家長教小朋友功課,尤其是讀字、默書,嘗試打破困局,除學術外也會聊天看書玩遊戲,建立關係。每星期一次在協會補習一至兩小時,疫情嚴重才改為 Zoom。Yolanda 又有向媽媽示範跟小朋友做功課:「做一陣玩一陣,比啲獎勵讚美。我知道小朋友鐘意Pokémon,就送佢一本那Pokémon 中文書,希望佢會自己睇。我又同佢玩一啲小遊戲,等佢返屋企同媽媽玩。」她說自己是小朋友的補習老師又是媽媽的聆聽者,她最希望媽媽也「聽」得見小朋友的心聲,但外人只能盡力而為:「我嘅貢獻係好少架渣,阿媽可能一樣都會打仔,只不過唔係我面前打,但起碼我同佢完成功課,佢唔會比阿媽𡁻,咁就OK啦。」
無聲的家庭,如何「聽」見子女的心聲?「香港聾人子女協會」網站連結了不少傳媒訪問,長大成人的聾人子女憶述他們艱難的童年,有個案說,他的聾人父母怕人歧視,不教他手語,甚至禁止他舉起手打手語,只由外公教說話,但因無法和父母溝通,關係疏離,小時候感覺缺乏父母的愛,總躲在角度流淚。有另一個案,憶述九歲時要幫父母打電話去銀行處理事務,但被銀行職員責備玩電話,要報警拉人,嚇得她哭濕了枕頭,又加上很多負面的情緒,她小四、小五想在窗台跳下去自殺,幸好都捱過。捱過了便有希望,兩個個案,長大後都有自己的工作和人生,在角落流淚的那一位,受訪分享如何照顧父母,修補關係;哭濕枕頭的那一位,叫「鄭詠恩」,受訪分享她在外地讀書遊歷,在港台主持聾人訪談節目。
「香港聾人子女協會」的創會會長陳佳儀,她亦是聾人子女,成長路絕不容易,所以他們一班同路人在 2013 年創立協會,希望能夠成為無聲世界的一道橋。協會為聾人家庭提供學習發展、輔導服務,親子教育等等,十年間幫助了超過 100 名聾人子女補習,並定期舉辦「心繫家庭」家長教育講座及工作坊等等,希望聾人家庭能建立更好的親子關係。陳佳儀說,聾人父母聽不到說不到,只靠手語溝通,所以小朋友一般也有語言發展遲緩,協會接到很多個案也有特殊學習需要:「父母吃力的,他們不知道怎樣教。學校可能很簡單去見家長,也溝通不到。老問問,為甚麼經常不交功課?為甚麼經常不及格?他們都應付不到,溝通不到。」
但無奈香港沒有聾人政策和相應的基金,陳佳儀說協會申請經費和捐助都非常困難,呼籲有人心出錢出力。協會現只剩下三四位義務補習老師,為大約 10 位同學補習。而 Yolanda 只做了補習老師一年,後來因為家庭和工作無暇兼顧,不過她說義工活動中有一系列生命教育和情緒輔導培訓,助人自助,祝願無聲的家庭能充滿愛。